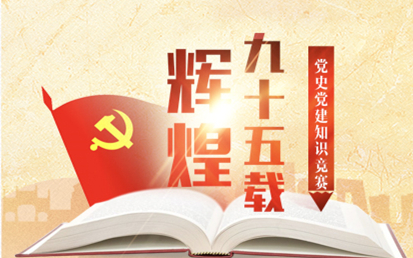他是共產(chǎn)黨員
2016年06月27日10:34 來源:北京日報 手機(jī)看新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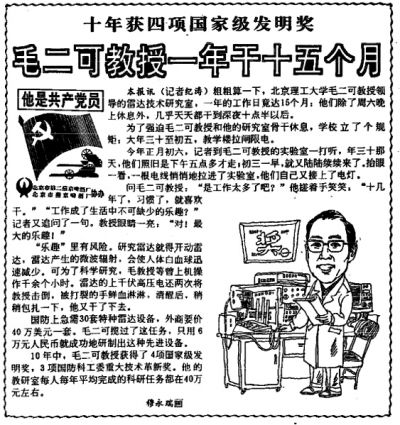
1991年3月31日1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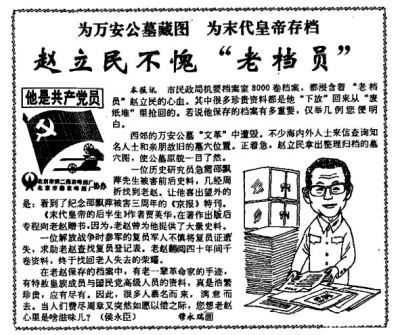
1991年4月12日1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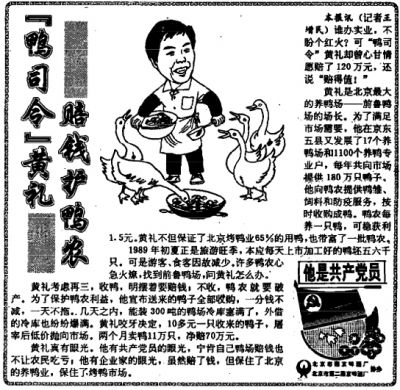
1991年2月10日1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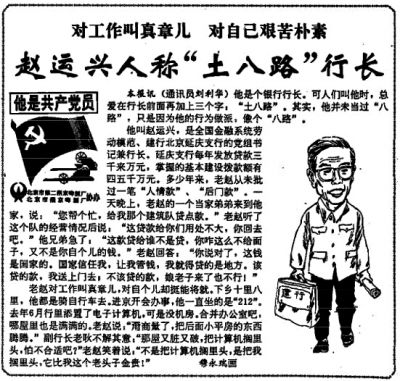
1991年6月1日1版

1991年6月25日1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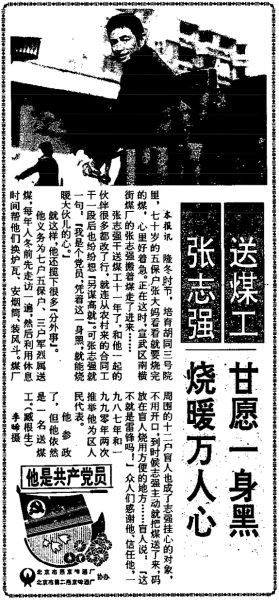
1991年3月1日1版
開欄的話
《他是共產(chǎn)黨員》,是25年前本報推出的一個人物專欄。從1991年1月1日至7月1日,每天一篇,筆端對準(zhǔn)首都各行各業(yè)的共產(chǎn)黨員,半年間,這個小小的專欄共刊發(fā)182期,勾勒出一幅流光溢彩的優(yōu)秀共產(chǎn)黨員群像。
今年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建黨95周年,全黨正在開展“兩學(xué)一做”學(xué)習(xí)教育。在這個時間節(jié)點,本報重啟《他是共產(chǎn)黨員》專欄,目的是接續(xù)傳統(tǒng),續(xù)寫新的歷史時期首都共產(chǎn)黨員的形象和風(fēng)采。
開欄首期,我們追訪了當(dāng)年寫過的幾位共產(chǎn)黨員。四分之一世紀(jì)過去,他們頭上添了華發(fā),人生軌跡發(fā)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,但共產(chǎn)黨員的本色如一。讓我們向他們由衷致敬。我們期望,有更多活躍在首都發(fā)展建設(shè)第一線,在各條戰(zhàn)線各個領(lǐng)域發(fā)揮著先鋒模范作用的共產(chǎn)黨員出現(xiàn)在我們的欄目里,也歡迎廣大讀者把你們身邊的好黨員推薦給我們,把他們的事跡介紹給我們。
辦好中國的事情,關(guān)鍵在黨;做好首都的工作,關(guān)鍵同樣在黨。群眾心目中黨的形象,直接體現(xiàn)在每個黨員身上。讓我們一起努力,來維護(hù)好、展示好“共產(chǎn)黨員”這個閃光的形象吧!
院士毛二可:帶隊創(chuàng)新
當(dāng)年的報道:北京理工大學(xué)毛二可教授領(lǐng)導(dǎo)的雷達(dá)技術(shù)研究室,一年的工作日竟達(dá)15個月。10年中,毛二可教授獲得了4項國家級發(fā)明獎,3項國防科工委重大技術(shù)革新獎。
追訪:75歲那年,毛二可院士“下海”了。他帶領(lǐng)的研究團(tuán)隊和北京理工大學(xué)共同組建公司,專攻科研成果轉(zhuǎn)化。
毛二可,在我國雷達(dá)領(lǐng)域可是響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拿帧!暗尭嗫蒲谐晒D(zhuǎn)化為產(chǎn)品,為國家服務(wù),一直是我的心愿。”毛二可告訴記者。
2009年12月,毛二可以自己和團(tuán)隊的科研成果作價600萬元入股,與理工大學(xué)合作成立理工雷科。為了表示與公司共興亡的決心,他拿出了全部積蓄,用于公司注冊。
公司成立后,團(tuán)隊中部分教師仍專注于基礎(chǔ)研究和理論創(chuàng)新,另一部分教師則利用公司推動成果轉(zhuǎn)化。所里那些被鎖進(jìn)柜子的科研成果,變成北斗衛(wèi)星導(dǎo)航基帶芯片、機(jī)場跑道異物監(jiān)測雷達(dá)等貨真價實的產(chǎn)品。
一位農(nóng)業(yè)植保專家主動找上毛二可,想定制一批雷達(dá),專門探測昆蟲遷徙,要求記錄昆蟲的大小、種類和飛行軌跡,觀測精度須達(dá)到厘米級。毛二可組織研究人員反復(fù)分析了項目的可行性,給出意見——“接!”與以前“老師+學(xué)生”的作坊模式相比,成立公司后團(tuán)隊研發(fā)實力已大大增強(qiáng)。去年,公司銷售收入達(dá)2.58億元,并成功并購上市。
毛二可仍是這個團(tuán)隊的“最強(qiáng)大腦”。每天工作8小時,周末、寒暑假亦不例外。這兩天,北京戶外的氣溫已達(dá)30多度,他仍戴著帽子、穿著白襯衣,在校園里指導(dǎo)學(xué)生做實驗。(記者 任敏)
趙立民:跟小廣告戰(zhàn)斗不息
當(dāng)年的報道:市民政局機(jī)要檔案室8000卷檔案,都浸含著“老檔員”趙立民的心血。其中很多珍貴資料都是他“下放”回來從“廢紙堆”里搶回的。
追訪:下樓扔垃圾的道上,趙立民隨手撕下了樓道里剛粘上的“空調(diào)移機(jī)”小廣告。
“見了就撕,環(huán)境就得靠大家維護(hù)。”85歲的趙立民常常感嘆沒有什么余熱可以發(fā)揮,但撕小廣告這件事,他已經(jīng)堅持了十幾年。
在哪里見到小廣告,趙老就撕到哪里。小區(qū)外面的路邊,公交站臺,地鐵車廂,甚至散步的公園,都是他清理小廣告的“戰(zhàn)場”。
有一回,因為撕小廣告,被貼小廣告的看見了,對方走過來威脅老人家。不過趙立民更高興,這下可以當(dāng)面“說說這些人了”。心平氣和、語重心長,趙立民從愛護(hù)個人衛(wèi)生說起,到愛護(hù)公共環(huán)境,再到維護(hù)首都形象,最終,貼小廣告的被說得灰溜溜地走了。
家人怕他和貼小廣告的起沖突,容易有危險。“一身正氣還能怕他們!我是老黨員,應(yīng)該教育他們。”
有時候,趙老會主動打電話教訓(xùn)貼小廣告的人。“貼到樓道里來,大家生氣還來不及,怎么會用你的服務(wù)!”一番話,還真能讓樓道清凈一段時間。
“咱是黨員,就應(yīng)該多管點事情,多管閑事就是服務(wù)更多人。”趙老說。(記者 童曙泉)
“鴨司令”:關(guān)掉鴨場開文化園
當(dāng)年的報道:黃禮是北京最大的養(yǎng)鴨場——前魯鴨場的場長。他不但保證了北京烤鴨業(yè)65%的用鴨,也帶富了一批鴨農(nóng)。他寧肯自己鴨場賠錢,也不讓農(nóng)民吃虧。
追訪:養(yǎng)鴨養(yǎng)了大半輩子,67歲的黃禮作出一個驚人決定:關(guān)閉鴨場,辦農(nóng)耕文化園。
黃禮一手建起來的順義前魯鴨場,曾是北京最大的養(yǎng)鴨場。這么大的買賣咋說停就停?黃禮說,養(yǎng)鴨影響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,索性徹底關(guān)停,還箭桿河一片清凈。
鴨場關(guān)了,在場里就業(yè)的村民怎么辦?黃禮早有謀算。“鴨司令”要帶領(lǐng)大伙兒轉(zhuǎn)行吃文化飯。
“我們前魯各莊村的歷史文化底蘊(yùn)深厚著呢。”黃禮翻出了《后漢書》,高聲朗誦其中的《張堪傳》。張堪,東漢期間任漁陽郡太守,曾在前魯各莊村開辟了北方第一塊稻田,“教民種植,使民殷富。”黃禮至今還記得小學(xué)一年級在張堪廟里上課,土廟四壁上都是農(nóng)耕圖。
可惜這座古廟已于上世紀(jì)50年代拆除,村里的水稻田也從1996年起全面退耕。
黃禮要把這份記憶找回來。他請來了專業(yè)設(shè)計公司,把養(yǎng)殖車間改成農(nóng)耕文化展覽館。他動手制作展示沙盤,依兒時記憶,再現(xiàn)村頭“清泉橫溢,綠水漫流”的美景。他遍訪村里的老人,整理與水稻有關(guān)的民俗、歌謠……
張堪農(nóng)耕文化園一點點雛形初具。“預(yù)計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試運行。”黃禮說,那時村里的鄉(xiāng)親們就可以到園子里就業(yè),捧上文化飯碗。(記者 王海燕)
趙運興:活到老較真到老
當(dāng)年的報道:他叫趙運興,是建行北京延慶支行黨組書記兼行長。他說:“國家信任我,讓我管錢,我就得貸的是地方。該貸的款,我送上門去;不該貸的款,娘老子來了也不行!”
追訪:“老爺子是不是真當(dāng)過八路軍?”“我看像……”這樣的議論,在建行北京延慶支行里常聽見。
大伙議論的老爺子名叫趙運興。1993年退休前,他是支行的黨組書記兼行長。他從沒當(dāng)過八路軍,只因作風(fēng)太像“八路”,大家給他起了個名字——“土八路”行長。
“這老頭子,‘鑿’!”提起趙運興,躺在病床多年的老伴兒蹦出一個字兒。在延慶話里,“鑿”就是較真兒、一根筋的意思。
剛退休那幾年,行里建家屬樓。趙運興向單位主動請纓:“建工程也需要有人監(jiān)督把關(guān),不如讓我這個老頭子來吧!”就這樣,花甲之年的趙運興又熱情投入了工作中。他蹬著自行車,每天穿梭于工地,認(rèn)真履行“監(jiān)工”職責(zé)。
一年后,新家屬樓建好了,行里的新老員工都?xì)g歡喜喜來看房,趙運興卻再也不來了——“我那老房子挺好,新樓還是留給年輕人吧!”
大塊頭電視、老式圓鏡子、碎花苫布……趙運興家干凈整潔,卻是個十足的“古董鋪”。他最珍愛的“寶貝”,是那輛黑色的“二八”自行車。每逢行里開會、舉辦老干部活動,都能看到80多歲高齡的他騎著銹跡斑斑的“二八”車來參加,再騎車離去。他執(zhí)意不肯接受開車接送。
這年頭,誰不知道新房好、汽車快?“別占公家便宜。”趙運興總是這樣教育兒孫輩,原來他“鑿”的,正是這個理兒。(記者 孫奇茹)
克里木:76歲送歌下社區(qū)
當(dāng)年的報道:歌唱家克里木從藝四十年,下部隊演出上百次,足跡遍及祖國的天涯海角。在舞臺上和舞臺下,克里木把自己的全部才華和熱情獻(xiàn)給了觀眾,也贏得了觀眾的深深愛戴。
追訪:“克里木,真是克里木!”4月25日上午,歌唱家克里木一邊唱著《掀起你的蓋頭來》,一邊踮起腳、翻著手腕,跳著熱情的新疆舞出現(xiàn)在海淀區(qū)北下關(guān)街道。社區(qū)里的居民驚喜極了,把他團(tuán)團(tuán)圍住,《達(dá)坂城的姑娘》《毛主席的戰(zhàn)士最聽黨的話》……一首首點起歌來。誰也沒想到,這位老歌唱家還活躍在舞臺上。
居民們的熱情感染了克里木,他沒有告訴大家,自己剛從新疆飛到北京,飯還沒好好吃一口就來到這里。一周多前,活動主辦方邀請克里木為居民做一場公益演出,克里木一口答應(yīng)了。沒想到演出前幾天,他又接到另一個到新疆慰問演出的通知,“沒關(guān)系,我都去,我坐夜里的飛機(jī),一點不耽誤。”當(dāng)天早上七點多,克里木在北京一落地,就直奔北下關(guān)街道。
連著幾天的演出,克里木都是吃著止痛片上場的。76歲高齡的克里木有腰腿疼的毛病,有時疼得走不了路。每到這時,他就趕緊吃幾粒止痛片,“控制住就行,不能在舞臺上出事。”
“我是當(dāng)過兵的人,也是五十幾年的老黨員了,不能軟塌塌的。”無論在哪里,克里木都充滿精氣神兒。近幾年,他依舊保持著每年五六十場的公益演出。“我是靠聲音為大家服務(wù)的,雖然我老了,但只要嗓子還好,我就一定繼續(xù)唱。”克里木常常這樣說。(記者 韓軒)
張志強(qiáng):當(dāng)樓門長服務(wù)街坊
當(dāng)年的報道:宣武區(qū)南橫街煤廠的張志強(qiáng)干送煤工11年了,他義務(wù)為7戶五保戶、3戶軍烈屬送煤,煤廠周圍的12戶盲人也成了他掛心的對象,不用開口,到時候就主動把煤送來,碼放在燒用方便的地方。
追訪:20多年前,白紙坊、牛街一帶的孤寡老人提起張志強(qiáng),都會豎起大拇指,“好人、實誠,有了他冬天不用發(fā)愁斷火。”如今,三廟小區(qū)14號樓的居民遇上難題,也會想到張志強(qiáng),“找張大爺,他一準(zhǔn)兒能幫上忙。”
張志強(qiáng)是原南橫街煤廠的工人。除了送煤,他還經(jīng)常幫助孤寡老人和五保戶做家務(wù)。退休后,他到社區(qū)當(dāng)起了樓門長。
三廟小區(qū)是老舊小區(qū),產(chǎn)權(quán)單位多,房主信息和物業(yè)信息很多都對不上,住戶遇上跑冒滴漏都不知道該找誰。張志強(qiáng)是14號樓的戊號樓門長,做的工作,就是幫助鄰里街坊解決這些繁瑣的“難題”。
去年雨季,頂層的房頂漏水,剛搬來不久的房主慌了神:找誰修?產(chǎn)權(quán)單位還是物業(yè)?怎么聯(lián)系?
對門的鄰居就說了一句:找張大爺,他能幫你解決。
張志強(qiáng)到了,拿出小本聯(lián)系了產(chǎn)權(quán)單位的機(jī)電公司。放下電話,張志強(qiáng)還跑回家,扛了把梯子過來,“我怕工人來了沒帶夠東西,不了解情況,耽誤修房頂。”
修理人員很快就趕到了。小半天的時間,房頂就修好了。張志強(qiáng)也跟著一起高興,“居民問題解決了,說明我沒辜負(fù)人家的信任。”(記者 李祥)






 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
 !
!